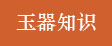中国古典雕刻的自由境界及形态分析
雕塑的发展历来脱不开与实用的关系。原始巫术中的祭拜圣像,实用与装饰结合的器皿、现代工业产品,乃至现代建筑等都是广泛意义上的艺术造型。在造型与实用之间历来有着密切的关联。
然而人们的类型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仿生”意念的支配与启发的,于是就有了“象器同体形态”的作品。这在东西方或南北方的雕塑史中作品众多。仿生,顾名思义首先是摹仿生命之物的形态造型,其次是其使用功能的应用,使观赏(或寓意) 与实用相统一。
中国的陶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都有大量的此类作品,无论其造型还是工艺都达到极高水平,甚至达到妙不可言的境地,但多以鸟兽造型为主。鸟兽雕塑在各民族艺术中之所以较发达, 原因 是鸟兽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人们从原始时代的石、陶器中即表现出对鸟兽的强烈关注。人们最初认为鸟兽是神奇之物,其奔跑、飞翔、撕咬的天性对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在蛮荒时代 ,鸟兽与人共同争夺生存的 条件与资源,于是人与兽之间也进行了漫长的殊死搏斗。为了生存,也为了猎获更丰富的维持生存的食粮,几乎所有的古代先民们都雕刻、绘制了大量的 祈望有效捕获猎物的“艺术”。但是随着人类以其无与伦比的智慧取得绝对胜利之后,再去雕刻与绘画动物时已不是最初的动机了。观赏、把玩、控制、驱使鸟兽的心理综合为一种创造“象器同体形态”的审美意向。人们把日常实用器皿,装饰物等首先制造为生动逼真的 雕塑造型,其次巧妙地设计“引流”(嘴)、“器物把柄”(尾巴或角)、“器盖”(鸟兽背脊或 翅膀等)、“器座”(鸟兽足)等等,使其完善统一。其 体量大者数百公斤,小者可于股掌间赏玩。其功用既有祭典之器,又有日用之物。诸器置于案几手边,随手使用这些飞禽走兽, 很可能滋生出主宰万物的心理。另外,各类禽兽动物千差万别的形体特征本身也具有装盛物品、容纳什物的功能性暗示,同时又因形而异,形成了极为丰富的造型样式。所以,其 创造的结果既是 造型生动之艺术品,又是方便实用之器皿,也是人类诸多民族传统艺术中观照自然、汲取自然因素的结果。成为最有特色的造型艺术之一。
由此种心理意向所趋使,人类虽然在告别陶器、青铜器之后,转而观照人自身并以此为主角地从事艺术造型达数千年,但在工业时代和高科技发展的今日,具有“仿生”意味的工业产 品仍大量出现。当然,最明了的如飞机,其功能的原理即是缘自飞禽,其外形的基本结构与飞禽并无性质差别。换言之,一架功能卓越、造型美观的飞机,何不可作为一件雕塑去看待 之呢?它着实是雕塑(如果略去它的实用目的)!除此之外,象形的、 非象形的产品远不止于此,建筑、车辆、山庄别墅之形更多地融入造型意味者也不鲜见。
由此窥观人类造型心理,功能(实用)与造型(观赏)同一,也即象器同体的心理自古有之,现 在有之,将来亦有之;况此心理最合中国天人合一观念,终究酿为一类独特之造型艺术。
(三)仿真再现形态
仿真再现形态的前提是,人首先用物质材料模仿出人或动物的真实物理状态,包 括比例、体积、骨骼、运动形态等,当这些物理量性指标悉数达到后,才能进入表达意思、 意义的环节。西方长达数千年的绘画与雕塑历程基本是此路一条的。
人类具有“仿真”的本能与天性。因为人类的眼睛在观察世界中最易被信赖之。所有“真实 ”印象的获得首先来自眼睛,所以当人们为表达意愿而诉诸形色时,自然也是以眼睛所见为尺度的。这一点人类皆同。
仿真的心理几乎伴随着人类之发展,尤以原始时代为其发育期。以为图像其物便能获得其物是所有原始艺术假巫术宗教方式而伴生的群体心理。二是仿真智能的生成与熟练在久远年代即有出色之表现。同时,随时间之推移,人类表达情思之范围日渐广泛,由来已久的媒介方式 (仿真图像)也自然固定为人类经久不衰的媒介体,终究到了能真实 “再现”人与物并达到逼真的程度。
为其代表者当属古希腊时代,其后的古罗马、文艺复兴、十八、十九世纪等近两千年的欧洲雕刻史中一脉相承,尽管每个时代以及某个时代中的每个雕塑家的风格各不相同,但其写实仿真的程度与由此获得的熟练技能,就石质雕刻说,是登峰造极的,代表了人类智能的一个高峰。
不仅如此,智慧不完全在于“仿真”,而于仿真基础上去表达意味与精神,这才是仿真形态的全部内含。从人物的体态运动、面部表情、性格特征、服饰质料到所有这些被 统一在确定明了的主题之下的完美谐和,每一个方面与每一个环节都被“艺术地”予以仿真性地表达。这自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仿真”,而是复现为生命力的仿真。
仿真技能的发育与成熟,反映了人类观照自身的兴趣与信心,历经数千年而不泯。在此观照中,人对人的认识加深了,在意欲刻划和所能刻划之间达到了最佳值。既可做到入木三分地性格刻划,又可巨细入微地尽情表现。
但是仿真技能与仿真风格的作品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受到瓦解与抛弃,似乎人们看得太厌了。于是突破以“真”为真的各种样式的艺术面貌又几乎张扬了一个世纪,但却又有了比古 典之真更真的“超写实”艺术。这正是“轮回”,但内涵已大异。
(四)意形似真形态
中国人认为天人应该是合一的,所以对待天地如同对待自己,互相渗透、互相消融。天地无常,人生无常,一切都似是而非。在中国人眼里,一切天然就是一切自然,而 “自然”合大道,是最高级的东西。所以对“自然”的认可之中包含了主客双方的因素,呈 现为模糊状态中的主客关系。最终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何求绝对的真?
于是,中国的造型艺术中没有认真的仿真,只有意与形相交织的“似真”。
中国的雕塑似乎一直是在意形状态中演进。其意依形而存,其形以意而设,互渗为既是、又非绝是的“似真”形态。换言之,从远古至明清的各类作品中,无论何种质材、何种功用 之雕刻品,绝无仿真之作,绝无毛发毕现,肌肉骨骼一如真人准确标致之作;但也绝无“ 非真”之作,绝无人非人,体非体,五官四肢易位或舍而去之之作。
然而,所有之形已被意之所浸,达到艺术表现最佳状态。这是中国古典雕塑的基本特征。当然,此说并非认为中国的“意形”特征是唯一正确,唯一高级之形态。相反,中国古典雕 刻中能被称之为绝妙之作者并不多,原因是大而化之的思维方式与似是而非的体悟方式是根植于整个民族中每一个人的群体无意识之中的,所以它天然地发生在每一个创作者身上,他 们仿佛天生地就具备了(也只能具备这样的)意形相融、大而化之、 似是而非的眼光与审美标准,并不需要经过理论的提高而加深对客观物理性质的了解,而是以手工经验加个人体悟作 为把握作品的调节手段,没有也不须建立以客观为尺度的依据。所以,除去功能的作用外,中国古典雕刻完全是因人而异的手工产品。
也正是缘于此,中国古典雕刻在某些时代条件下,其“意”的表达才能最大限度地不受“形 ”的制约,更多地融入创作者主观的意向,使其跃入佳境。如唐帝陵的狮子,无一只与原真狮子相像,然而却无一只不“是”狮子,无一只不比真狮更赋神采,更具精神。但如果细察 唐十八陵中一百五十余尊各类狮子,却绝少重复。单是毛发便多种多样。这就是因人而异的 自由状态下的结果。这颇似中国画中之写意方式,意为纲,形为目。“纲举目张”。
(五)结构物质形态
在这里,“结构”应作动词理解。它不是指结果的状态,而是指“结构地”处 理物质的方式。我们现在通常所说所见所做的所谓“抽象雕塑”即是。
抽象是一个相对方便的说法,主要是针对“具象”而言,但并不确切。因为它的本义是哲学 意义上的理论形态,而在造型艺术中无论是怎样的“抽象”,都是长、方、圆、不规则形状 的 实在的“具象”。在这里所“抽”去的象只是指用物质方式模拟自然的物象而已。而作为非 仿真性的雕塑造型来说,它仍具有着一个“被结构了的”造型之象。这便是结构物质形态的雕塑。
可以说,一切非仿真性雕塑之外的物质结构体均 属此类作品,当然还有一个前提:以审美为主要目的。这便是桌子与雕塑的区别。
结构物质形态的作品,缘自人们对形体本质的认识。人类由用物质材料绞尽脑汁地去仿真自然物象,到逐渐地舍弃它,而代之以还原为物质原始形态本身的结构原理,是人类对物质与 造型的飞跃性认识。当人们在无力加工原始材料的原始时代,人们是被动于物质的;而今天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用各种质材去探索纯属于结构与空间的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这场革命起源于欧洲的现代艺术运动,也得助于工业革命与科技进步的时代。至今至少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在这个世纪中,人们探索出了极为丰富的艺术样式。人们认识到,作为艺术的视觉造型是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的,并且它的效应不仅在于自身的完善 ,也在于它同人、建筑、空间等环境因素相关联的关系。其意义已超出了“美术”的范畴。
结构物质,使结构成为造型艺术的“文本”,无疑拓宽了视觉艺术的领域,使其具备了更宽 泛的含义与表现张力。也使艺术从长期肩负的如道德、宗教、教育、纪念等历史的重任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更灵活更丰富的天地。在视觉贯性上,它阻断了旧的样式,同时又向人们提供了不断更新的样式。时至今日,人们似乎并不关注作品本身的含义如何,而作品与环境的谐调、与人匆匆一瞥中的视觉感觉,似乎是“结构”艺术的命脉了。
综上所述,我们粗略地回顾了迄今为止人类在造型艺术(雕塑) 领域中开辟出的五大基本形态。正是它们构成了皇皇然一部庞大的雕刻史。然而却是包含了古今中外、东西两大体系中的基本内容。任何一种形态的产生并被人类所应用都是旷日持久的。它绝没有某一种思潮、某一种观念来得快,但也不会消失得快。这说明人类使用的“语言”是单 调而漫长的。另外,多种形态也并非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一旦由生发而产生,便各得其所地被人们所使用。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新形态的作品仍会出现。它不因人们预言而出现,也不由人们意志为转移。
|